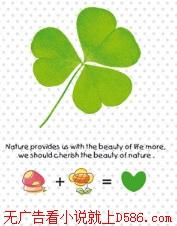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失联牛航的幸存者 > 第23章 白雪公主和大胡子(第2页)
第23章 白雪公主和大胡子(第2页)
她说:这个问题你也问过。可是我也是说不出来的。因为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来了多少年了。这里看不出四季,不下雪,也不会太热。我这个人过日子本来就稀里糊涂的,过着过着就把日子过丢了。
她说过丢了,挺童话的,我想。
我说:你爸爸也不记得日子了吗?
她说:我当年前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我爸爸。这么多年下来,我一次也没有见到我爸爸。我问过,问过很多人,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不肯说,也许是不肯说。
我说: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她说:是大学教授。教哲学的。许多人称他为当代恩特思。
我很惊讶:教哲学?当代恩特思?我听说过啊。他的姓名是个格曼姓名,他叫托马斯。麦牙。是他吗?
她说:对的,是他,你知道他?
我说:听说过。很有名的。可他是个白人。
我发现我失口了。我绝没有歧视任何人的意思。我从来就认为全世界各民族各肤色的人都有聪明美丽高尚的人,当然也都有不聪明不美丽不高尚的人,完全不因民族或种族而有别,只是因人而异。
可纳丝林毫不在意。她说:是白人啊,我妈妈也是白人,他们都是从格曼来的第一代移民。所以他们才会生出一个白雪公主啊。
她在行走和说话的过程里第四次转过头来(不好意思,我喜欢数数),我看到她油黑发亮的脸上油黑发亮的眼睛里闪出油黑发亮的光来。
她这第二次提到白雪公主,给我的感觉跟我第一次听到完全不一样了。
难道,她有色盲?她竟然不知道她自己的长相?即使没有镜子,可是自己的身体、手和脚总是看得到的。
可是出于良好的家庭教养,毕竟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没有在这个方面深挖下去。我甚至转移了话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还不等我把话题转移好,实际上我只开了个头,一道门在两边贴脚线发光的过道的尽头裂了开来。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道楼梯。向上的。
我真想跟这位黑皮肤的白雪公主多聊聊,可是,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再好的晚宴也有吃完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地面上,一栋大楼的底层。
她敲了敲一扇门。她是脱下手套,用素手去敲门的。
我惊讶地发现,我是第一次看到她的手。她到我的极简空间来送饭,永远是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全身穿着白色的酒店服务员那样的制服,两手戴着白色的手套。
我没有时间去思考问题,因为那道门已经开了。
纳丝林再次给我鞠了个躬。
房间里没有声音。
我站在门框里,眼前是一个宽敞的办公室。房间里有一张大办公桌,一张老板转椅。
没有人。老板转椅却在微微地转动着。
我想问纳丝林这里的人呢,可是纳丝林只是注视着那个微微转动着的转椅。好象在等待那里转出什么来。
还真是的。一个脑袋从桌子后面冒了出来。一个硕大的脑袋,一个几乎全部被毛发覆盖了的脑袋,客观地说,是那胡子特别的浓密,眉毛也特别的粗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