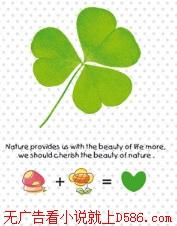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限时暧昧[追妻火葬场] > 第31章 Chapter 31(第1页)
第31章 Chapter 31(第1页)
一晚上经历太多,精疲力尽的怀芷上车没多久,眼皮就开始打架,后来她实在撑不住,闭上眼睛想小憩片刻。
结果直接睡了过去,还顺便做了个很长的梦。
在梦里,她回到五年前的那个不眠之夜,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尖叫声充斥整座医院,不断有担架车将爆炸案中的伤员送进抢救室。
医护人员大喊着,让无关人员让路站到一旁,推着担架车脚步飞快。
那一晚,死亡笼罩着整座医院,担架车上的人奄奄一息,黑红的血顺延而下,一颗又一颗地重重砸在地面。
怀芷还清楚记得,那时她刚签完两份死亡确认书,甚至还来不及感伤,怀游的病危通知又飞雪似的一封接着一封。
停尸间里躺着两具她最亲密的尸体,不久后就要被火化成灰。
掀白布时,她的手筛糠般颤抖不停,鼻尖满是烧焦的刺鼻气味,最后还是旁边的护士实在看不下去,替她将白布拉下。
腐臭味扑鼻而来,怀芷却没有抬手去捂抠鼻,出神地怔怔望着面目全非的两具死尸。
不苟言笑的父亲、温婉贤惠的母亲,一动不动平躺在冰冷坚硬的铁皮面上,悄无声息,再也不会开口和她说一句话。
不断有人上前安慰,怀芷只是呆呆站立原地。
耳边不断有悲痛欲绝的哭声响起,她却一滴泪都哭不出来,甚至感受不到悲伤,只是觉得呼吸有些困难。
她想,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生日。
离开前,怀芷闭着眼深吸口气,在死寂般的密闭房间内,轻声说了两句话:
“对不起。”
“如果怀游还活着,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请你们放心。”
深夜将近凌晨,整座城都陷入沉睡时,医生才终于从抢救室里出来,满面疲倦,神色却是如释重负。
“命保住了。”
怀芷听见医生这样说。
医生还说,按怀游距离爆炸点的距离,本不可能有生还的机会,但情急之中有人用身体死死护住了他,这才得以保命。
只不过大脑皮层依旧严重受损,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怀芷看着重症室里满身插管的弟弟,精神恍惚地来到走廊尽头。
明明昨天还一切如常,她还能回想起,弟弟背着她和父母偷偷商量,如何准备她十八岁的生日惊喜。
胸腔好像被人掏出一个大洞,将最重要的部分抽离剥离,怀芷觉得她整个人都是空落落的。
很久之后眼前突然一黯,她才听见自己压抑至极的呜咽声,以及泪眼婆娑中,递来的一方冷灰色方形手帕。
那只手单薄而修长,骨节凸起根根分明,冷白皮在灯下格外晃眼,像是精雕细刻的艺术品。
怀芷傻愣愣地抬头看,泪水将精心打扮的妆容晕染,米白色的棉质长裙沾着血迹,狼狈至极。
面前的年轻男人沉默着和她对视,他站在逆光处,看不清楚五官样貌,但只看那双淡漠深沉的黑眸,就知道他一定是极好看的。
犹豫片刻,怀芷迟疑着接过男人的手帕,纤软指尖触碰到对方皮肤传来的温热,然后无法抑制地,泪水再次决堤。
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她寻着温热顺势而上,紧紧攥住男人衣袖,恐惧又无助地不肯放手。
“可不可以别走,陪我待一会吧,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