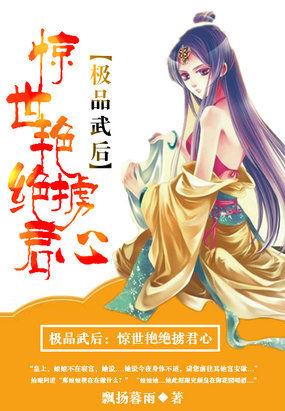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点点福运来 > 第111页(第1页)
第111页(第1页)
阿福接过瑞云捧来的茶递给她:“阿馨,你想什么呢?”李馨接过茶,摇了摇头:“也没什么。”阿福知道她多半是在担心她的母亲和弟弟,可是这种时候如果说什么吉人自有天相的话,那也实在没有什么用处。她只是安静的坐在她旁边。——朱平贵也在城中,不知道他能不能安然躲过这一劫。蛮人……蛮人是不会讲什么仁义良善的,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京城经过这场浩劫……只怕是全毁了。来日,又该怎么办呢?阿喜和朱氏也已经起来了,阿福站在窗边看到阿喜出来泼洗脸水,小院里现在住的这样挤,但是却非常安静,一个高声说话的也没有。这种异样的安静并不让人觉得温馨,反而透出一股浓重的压抑。阿福见着了他们说的那位高公子,这人和想象中——不太一样。阿福所知道,见过的世家公子不多,象韦素和韦启,李固和刘润也勉强算上吧,都显的有一种超逸的文雅之气。可是这位高英杰公子——人如其名,有一股子英气,个子比李固还高一些,宽宽的肩膀,眉毛又黑又浓,象是蘸足了墨的狼毫笔从眉心用力的朝两边划出去,直至鬓边,看人的时候有种不怒自威的架式,阿福隔着帘子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人不象个郎官家的公子,倒象是武将家的少爷。李固问他伤势如何,他摸了一下肩膀说:“不碍事,小伤。”“虽然箭没有射进肉里,但划的也不轻。”刘润说:“等下再换一次药吧。”阿福这才知道这人昨天也受了伤的。他们接着说起外的形势来,面色都很严峻,阿福听了两句便没有再听。这些事她帮不上忙,白担心事。她的裙带已经系的松松的了,李信好奇的盯着她的肚子一个劲儿的瞧,瞧的阿福脸上抹不开,而瑞云紫玫她们则偷着笑。阿福瞪了一下眼:“不许笑了。”紫玫怕她真恼了,岔开话说:“我刚才点了下粮食,搬过来的虽然仓促了些,但是也够我们吃到开春的,就是夫人没多少零嘴儿了。”“我要什么零嘴儿,倒是阿信……”“夫人现在双身子,不一样嘛……”阿福找了几件没穿过的鲜亮衣裳让紫玫给李馨送过去,结果门帘一掀,李馨托着那个包袱又给还了回来。“咦?不合穿吗?”“这些衣服都暖和,该嫂子自己留着穿才是。”阿福说:“你只管穿,我这儿还有呢。”李馨打开包袱,把一条裙一个斗篷挑出来,剩下的两件又包起:“这就够了。”阿福看她眼圈儿红红的似是哭过,心中留意,嘴上却没说什么。李馨说了一会儿话回西屋去,紫玫低声说:“刚才我送衣服过去,王爷正和三公主说话来着,三公主见我进去把泪抹了,不过我看见了。”阿福叹口气:“要是换了我,我也得难受啊。她母亲和弟弟,还有皇上都……”阿福把生死不明咽下去,说:“都下落不明。”紫玫摇头:“不是的夫人,不是为这事。”阿福讶异:“那为什么?”紫玫摇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不是为这事儿才哭的。我就听见三公主说了半句‘这难道是我的错么?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其他的就都没有听到了。”阿福想了想:“你去叫刘润进来。”阿福的经验很管用,有什么事情不知道不懂的就去问刘润,他简直就是百事通,没什么他不晓得的事。雪一停,天反而冷的更狠了。阿福坐在炕边,屋里拢着炭盆,瑞云掀起帘子,刘润走进屋来。他大概刚从屋外回来,脸冻的煞白,只有鼻尖通红。平时这个人都显的老成,今天这么一看,那个红鼻子倒是显的他很有些稚气。阿福让瑞云在门口守着,低声问刘润:“你可知道三公主为什么事情那么伤心?”刘润却与她同时开口说:“我替你把一把脉。”阿福一笑:“常太医隔一天也替我把一次脉,我好着呢。”虽然这么说,瑞云替她捋起袖子,刘润替她诊过,点头说:“还好,我只担心变乱一起,你担惊受怕于自己和胎儿有损,这样看来还好。”“三公主的事,你知道吧?”“嗯,其实三公主从太后二次被幽禁之后,日子很不好过。这事儿还得从上次王爷同你进宫说起。那天太后的提婚被王爷断然拒绝,面子抹不开,三公主为了让太后同意给宣夫人请太医治病,也为了保哲皇子一条命,向太后自请,愿意替哲皇子作主娶王家的那位王容姑娘。”呵……还有这等事?没人和阿福说起过呢。“那……后来怎样?”“刚交换了婚书,皇上已经重掌大权,太后重又下狱,不止三公主,整个玉岚宫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宣夫人缠绵病榻,一半倒是心病。哲皇子抑郁暴燥,三公主眼见是失了宠……”平心而论,阿福能理解三公主的作法。她对母亲是孝敬,对弟弟是爱护,可是她那个决定,就算是权宜之计,皇帝也很难原谅吧?“你说,你们出宫时被她拦住,所以一起回的府,她就是为这事儿去找王爷商量的吧?”“是,三公主的意思,大概是想请王爷替她在皇上面前求恳讨情儿,只是没料到……”是啊,现在讨不讨,都不重要了……宣夫人,哲皇子,还有皇帝,他们在哪儿,是不是活着……这还是未知数呢。“你昨天……没受什么伤吗?”刘润愣了下,笑着摇摇头:“我没事。”阿福始终有点不太放心,可刘润却说让她只管放心。“对了,京城明明不该这样不堪一击,蛮人怎么那么轻易的进了城呢?”刘润默然,半晌没说话。阿福试探着问:“是不是……有内应?”严寒(二)刘润最终也没有告诉阿福。其实说不说,都一样。会与皇帝对立,宁肯打开城门放蛮子进城玉石俱焚的人,还会有谁呢?阿福确切来说,并不算这个时代的。她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也与此时的人有不同。对于忠君二字,她没有什么太深感触。可是这并不代表,她能心平气和的看待京城之乱。王家和皇帝的争斗,那是他们的事,可是放蛮子进城,害的是全城百姓。因为一己之私,拉全城的人陪葬——如果说还有人比烧杀掳掠的蛮人更丧心病狂,那一定非王家人莫属。阿福吃了半盏茶,听着外面朱氏和瑞云说话,虽然声音都不高,可是屋子小,人挤迫,谁打个喷嚏一院子的人都听见了,还有什么秘密隐私可言。朱氏问:“瑞云姑娘可见着我家阿喜了?”瑞云说奇怪的说:“阿喜姑娘?她没来我们这屋啊,夫人找她?”朱氏低声说:“刚才她说头痒,要烧水洗头。我没说帮她,她说她自己提雪烧水去——可是这一会儿了,怎么都没有见着她?”阿福也暗暗纳闷,这里只有这么点大,出了院后,后面没几步路就是个小瀑布,而前面的石头那里是没有人去的——外面天寒地冻,阿喜难道为了和朱氏赌气就甘愿在外面挨冻不成?“屋后我去看了,没人……”朱氏的声音有点抖。瑞云也愣了:“是不是……她生您的气,故意躲起来了?”“她能躲哪儿去啊?”朱氏慌了:“总不能……哪里有冰窟窿她掉下去了?”瑞云的话也没底气:“这……该不会的,唔,我陪您老再出去找找看。多半阿喜姑娘是赌了气躲气来了,您先甭着急。”阿福听着她们开门出去,过了盏茶时分又回来,这会儿朱氏倒不吭声了,瑞云念叨着:“怎么会呢?怎么能不在呢?这里又没有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