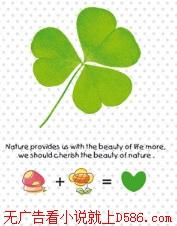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禁界李宇春 > 第153章 魔鬼(第1页)
第153章 魔鬼(第1页)
大海上,一艘破旧的帆船正迎着暴风雨,逐浪而行。
海浪很急,在狂风暴雨的扰动下仿佛一锅煮沸的开水,无数浪涛起起伏伏,将一艘并不如何结实的帆船抛上复又抛下,让人忍不住替那木头制成的东西狠狠捏着一把汗,生怕它一不小心就在空中散架了。
船舱里,老船长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冲着大副狂吼着“左满舵”。而在甲板上,几个船员如同风中的柳絮,紧靠一根绳索捆住腰身,在浪里浪尖拼命的搏斗着,降下船帆,拉紧船舷。
而在船上最高的那座瞭望哨里,此刻却正站着一位女子。与下面衣着破烂的船员们不同,她身上的衣物很新潮,紧身的黑T恤外加修身的牛仔裤,那玲珑的曲线和高挑的身段暴露无遗。
她似与整个画面极不协调,虽然站在整艘船最为危险的瞭望哨上,却仿佛仍旧置身事外,只是有些冷漠的俯视着下面正在发生的一切,眉头微蹙。
“第几次了?”女子开口自言自语,是标准的纽约味道。女子正是南亚。
她看了看自己左手边被指甲刻出来的痕迹,而后恍然道:“第二十次了呀,看起来,这艘船确实坚持不了多久了呢。”
果不其然,当她话音刚落的刹那,一道巨大无比的浪头忽然当头轰落。“轰隆”一声,船上第一根桅杆应声折断,连甲板也被砸出了一个硕大的窟窿,海水汹涌灌入。
船长发疯似的对身边人大骂着,让他们赶快去修补破洞抢救物资。虽然他也知道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如果永远都无法抵达目的地,那这一船物资就是再如何价值连城又有何用?
几个小时的辛苦搏斗,当暴风雨散尽,海面重新出现阳光时,整个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累得瘫倒在地,再也不想挪动一个指头。当然,南亚是个例外。可她严格来说却也不能算是这艘船上的人,因为没人看得见她,仿佛她只是个透明而来的看客。
突然,站在船头的一名船员一声大叫,声音带着哭腔的喊:“快看!快看那座该死岛!我们又回来了!又回来啦!”
闻言,饶是所有人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却仍旧挣扎着站起身来,而后看着远处那座半隐在浓雾中的岛屿沉默不语。
忽然有人无声的啜泣,紧接着便是一片席卷全船的嚎啕大哭。便是那名一直都处变不惊的船长都狠狠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颤抖着双手想要点烟,可他却始终拿不稳那支精巧的烟斗。
“该死的!不走了!我们回到那座岛上去!回去!”船长愤怒的骂了一声,立刻让船员们再度忙碌起来,小船微微调整了一下方向便升起船帆向岛屿航行而去。
第二十一次,帆船“普爱思”号试图离开禁界,失败。
在船上那座瞭望哨里,南亚轻轻扣下指甲,在那块木头上又一次刻下了一道痕迹。面无表情。
接下来的几天里,船员们的情绪始终都处在失落与亢奋的交杂之中。他们开始暴躁易怒,开始反复无常。第三天时,几个船员一起杀死了另一个人,原因似乎只是嫌他太过聒噪。第五天时,船员们已经杀红了眼,所有人的手掌上都多少沾了一点血。这时,他们还仅仅剩下五个人。
而这时,在最需要船长大幅们来主持大局的关键档口,船长本人却自己携带着一柄燧发枪与一本航海日志离开了驻地,孤身一人向岛屿深处而行。
他不知听到了什么声音在召唤,虽然害怕却仍然忍不住心中的好奇与憧憬。终于在挣扎了几天之后选择抛弃那些船员,孤身上路。
他相信,在那声音的尽头,一定有能够离开这座岛屿的方法。至于为什么这么笃定却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身后,南亚方法幽灵一般漂浮而行,静静跟随着他的脚步。
穿过那片熟悉的沙滩,走过那片眼熟的森林,绕过那颗不知如何才能长成这般高大的鬼树……在一个晨光希露的清晨,船长在森林里看到了一个人。
没错,一个人。
不是他的船员,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另一个人。径自出现在了通道中央,仿佛早已等待船长多时。
“你终于来了……”那人微微开口,笑容竟是说不出的狰狞酷烈。这时,船长和他身后的南亚才发现那人手中还提着一柄刀,那刀锋上似乎还有血,正在滴落的血。
“你终于来了!”那人重新说了一遍,船长却掉头就跑,再也不顾心中期冀的逃生之路。追与逃在刹那间开始,一开始就让人大跌眼镜。
那人似乎是在做一场游戏,明明以他的速度轻而易举就能追上船长,可他偏偏却一刀刀的不断在船长身上添着伤口,眼看着他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人似乎笑的也就越是畅快。
南亚看不清那人的面孔,无论她怎么靠近都看不真切,哪怕就在那人身前时仍旧觉得那人的脸庞始终都被笼罩在了一层浓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