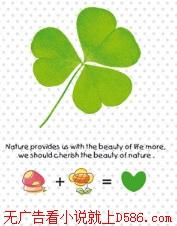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亲爱的苏格拉底言焓和沈弋 > 第103章 chapter103(第2页)
第103章 chapter103(第2页)
他心一紧:“你先说。”
她又默了,过一会儿,闷闷地唤他:“队长。”
“嗯?”
“你找我有事吗?”
“……你……身体怎么样?”他嗓音极轻,温柔得像生怕吓到她。
“挺好的。”她听上去不悲不喜。
“胃口呢?”
“还行。”
“睡觉睡得好吗?”
“……一般般。”
“会做噩梦吧?”
“……”不吭声。
“不要怕。”
“……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
“……嗯。”
又是良久的沉默,他望着玻璃外漫天的风雪,眼睛微微湿润,说:“那你好好休息,挂了。”
“……嗯。”
双方安静着,都没有先挂电话。
言焓眼眶红了,又说:“别躺太久,也下床走走。”
“好。”那边怔了一会儿,喃喃,“队长……”
“嗯?”
“……我上次说的有些话……”太伤……
“没有。”他打断,不愿她自责。
“……”她哽住无言,良久,终于轻轻道,“下次你来看我,我们……我……好好说话。你……也要和我说清楚。”
当爱情与信仰不可兼得,她毅然说:我爱你,但我不会和你一起,我以后一个人过一辈子。
可发泄与冲动过后,她终究是……
他眼眶里的水差点儿模糊视线,她的心,依然对他柔软。
他甚至有种错觉,她给他的温柔,比沈弋多。
“小猫,”他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那边没吭声,呼吸渐渐局促:“你说……”她立即打住,竟不敢重复那个字。
“是。小猫。”他说得缓慢而认真。他爱她,他早应该让她知道。
她似乎窘迫,忙说:“挂了。”然后却等着。
他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