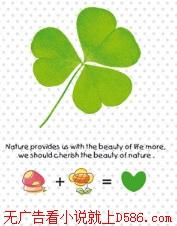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闺宁书评 > 第241章 反戈(第1页)
第241章 反戈(第1页)
窗外夜雾未消,此刻尚不过卯正。
谢姝宁整夜未曾阖眼,原本眼皮沉重,难得有了丝倦意,而今一听到这话,登时睡意全消,忙问:“都说了什么?”
卓妈妈小心翼翼地回道:“说是已找到鹿大夫的所在了,只是要将人给救出来,怕还得费一番周折。”
“我亲自去见他。”谢姝宁眉头微微一皱,准备亲自去见鹿孔。
冬日的天总是亮得比较晚一些,天上积聚的云层也总仿佛厚实些,不易被金灿灿的日光穿透。外头的雪已停了,但化雪之日比落雪时还要冷上许多,卓妈妈不敢掉以轻心,一等谢姝宁准备起身,便立即打发人去取了极为厚实的冬衣来,将她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冬至眼下人在何处?”谢姝宁匆匆自盥洗室出来,喊了玉紫来梳头。
卓妈妈道:“在二门外候着。”
谢姝宁颔首,只让玉紫随意将长发一梳,便命人取了鹤氅,戴上风帽出了门。
得了消息,原本该立即去知会月白一声的才是。
但月白昨夜累极,却强撑着不肯睡去。
谢姝宁无法,恐她败了身子,只得半夜让人悄悄在她的屋子里点了安神香,这才让她沉沉睡了过去。因而这会,谢姝宁便没有唤她起来,只身带了图兰飞快往二门外的那个小亭子去。
灰蒙蒙的天,待她们走至亭子附近时。才算是亮了些。
就着这点光亮,谢姝宁看到亭子里并不止一个人,不由脚步微凝。
除了冬至还有谁?
思忖间,亭子里的人也瞧见了她们,往外走出来迎了一迎。
谢姝宁直到这时才透过正在消散中的薄薄雾气,看清楚了候在亭子里的那几人。冬至自然在,可他身边却多了个谢姝宁没有料到的吉祥。
不及她们再靠近,气氛便陡然一僵。
不知是不是因为要进谢家来的缘故,吉祥身上此刻并没有佩剑。
图兰打量了他几眼。没动,对面站着的吉祥也没动。谁也不出声,事情就变得怪异起来。谢姝宁无力扶额,无心知道这二人之间的矛盾,只拔脚往亭子里走,趁着微明的天色。上了台矶,立即问道:“鹿大夫此刻人在何处?”
冬至看了一眼吉祥,而后才道:“约莫寅时一刻时,奴才一行人同吉祥大人的人,遇上了。”
“我只是个护卫,不是大人。”话音落地。吉祥淡淡解释了句,“鹿大夫在富贵巷里。”
冬至脸皮一僵。斥了声:“怎好在小姐面前说这些!”
富贵巷这样的地方,说出来未免脏了官家小姐的耳朵。
即便冬至知道谢姝宁不同,也秉着做下人的规矩,死死不敢直接在谢姝宁跟前将那地方给说出来,故而方才卓妈妈知道了具体的地方,也不敢告诉谢姝宁。他们都清楚自家小姐的性子,万一她想亲自前去富贵巷救人。可如何是好?
在吉祥这,却没这么多顾虑。
富贵巷的名声太大。满京都从老到少谁人不知,在场的人里头,真的不清楚的,也唯有一个图兰而已。
见吉祥的话说完,谢姝宁面带惊讶,一个字也不说,图兰不由急了:“小姐,我们既然已知道了地点,不如赶紧过去吧!”
谢姝宁一下在石凳上坐下,手指扶着冰冷的石桌沿角来回摩挲,思量着说道:“不是你我能去的地方。”
她倒是真的没有想到,人竟然会在富贵巷里……
一条街的花楼,鹿孔父子又会被藏在了哪间里头?
犹如针入大海,汪洋之中,踟蹰难寻。
豆豆还那么小,正是爱哭爱闹不愿听话的年纪,被藏在了富贵巷中,实在不像样子。
她惊疑不定地抬起头来,看向吉祥:“富贵巷里,有万家的产业?”
那些个老鸨龟公,个个都是老奸巨猾的东西,轻易不可能会收旁人控制,即便是位高权重之人,也艰难,但若是老板下的令,那便不同了。可万家的人,自诩清流,焉会沾染这些东西?
“万家、燕家都没有任何同青。楼赌。场粘连的地方。”吉祥想也没想,断然否决,“这件事谢八小姐暂时不必碰触,主子那自然会给您一个交代。”
若非燕淮让他亲自来同谢姝宁解释提醒几句,他才不愿意跑一趟谢家。
毕竟既然牵扯到了富贵巷,不管谢姝宁做什么,一旦被人知道,于她的名声终归是有损的,绝不会有好事。
吉祥无奈,只能领了命令赶来,“鹿大夫父子性命无忧,还请八小姐放宽心等待。”
谢姝宁听着,忽然讥笑了声,“放宽心等待?我的人好端端被抓,如今尚且生死不明,你叫我如何放宽心?”说完,不等在场诸人回过神来,她蓦地一叠声质问起吉祥来,“燕二爷病了,快死了,与我们何干?你家主子既然已重回燕家,手掌大权,为何不好好将人看牢了?连个病入膏肓的人都看不住,他还妄图成什么大事?万家的人既无产业在富贵巷,那他们又为何会藏身富贵巷?你满嘴谎话,还叫我宽心?”
她一声又一声地诘问着,吉祥一时不查被唬了一跳,连退两步,被冷风一激,方才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