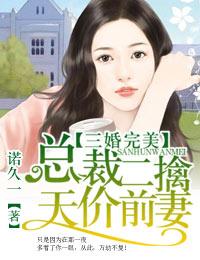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穿越到楚汉时期 > 第49章 重要支持(第4页)
第49章 重要支持(第4页)
“那依你看,朕要派何人将兵,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嬴政问李斯。
“大王,”李斯回答,“臣以为非王翦将军不可。”
“王翦带兵,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到神奇的地方,也很少有特别令人赞叹的战斗。”嬴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奇谋之将,看似才能出众,然而兵形险招,若有不测之事,便是万劫不复。”
“大王认为大将军不会奇谋,而战争的根本从来就是战前的准备和谋划,谋定全局,让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这才是最稳妥的战斗方式,而这正是王将军的长处。”李斯回答嬴政。
“如果给他十万人的军队,他无非也就是能打出十万人的效果。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嬴政又说,“就没有更加有本领的将军了吗?”
“大王,”李斯回答,“兵不在多,而在精。军队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人越多,产生的矛盾越多,管理的难度越大。”
“完全不懂领军之法的人,任性妄为,会使得士兵之间矛盾重重,虽有十万之兵,却似乌合之众,一但遇敌,便会做鸟兽散。
“而一个普通的将军,带领着十万人,能够打出十万人的效果,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人再多一些,管理的难度十倍百倍,常常不到打仗的时候,自己就要出问题。
“王翦将军看上去没有出众的才华,但老将军的本事正在于给他多少军队就能发挥出多少作用,而不会大打折扣。这是老成持重,是他人难以复制的本领啊。”
“大王若要一战而并吞楚国,一定要信任王将军,君主和将军一心,才能使得军队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大王,为了大秦的一统,请您三思啊。”李斯说。
“那,倘若这六十万人,临阵倒戈,朕当如何?”嬴政问道。
“大王,”李斯没有直接回答秦王的问题,他反问道,“您认为人的行为,最根本的动机是什么?”
“是什么?”嬴政说,“廷尉有话不妨直说。”
“是,”李斯回答,“圣人贤者对人的行为有千百种要求,却不知人最根本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利。”
“从士兵的角度来说,秦国的士兵积累战功,在秦国不用交税,更兼一家老小都在关中,一人背叛,全家遭殃,谁会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对于领兵的将军来说,六十万人就是六十万张嘴,粮食给养皆自秦地供给,一旦倒戈,不出月余就要粮尽。几十万饥饿的士卒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倒戈对于将军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而其他国家,先不说国运已经衰败,主上无有争心。即使有心,想要收编秦国的军队以为己用,国家也没有能力供养这么多军队,谁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好!”这才是真正解答了嬴政最为关心的问题,秦王觉此计甚妙,于是拍案而起。
“廷尉所言即是,”嬴政说,“接见使团的事情朕再推一日。明日就去请王翦出山,朕亲自去。”
“是,”李斯说,“大王英明盖世,实乃大秦之幸。”
“待破楚之日,廷尉便是最大的功臣。”嬴政说,“李由的事朕知道了,明年朕亲自推荐他,看看谁还敢动手脚。”
“大王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李斯略微有些惶恐的说。
“下面人的事情朕心里都有数,”嬴政说,“李廷尉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朕,朝中没有人支持你,那朕来支持你。”
“同样的,当朕没人支持的时候,你也得全力来支持朕。”嬴政说。
“是”李斯回答,“谢大王。”
嬴政带着内侍离开了,李斯则瘫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李大人,”蔡止过去扶李斯,“大人,大王这样替您着想,您不应该开心吗?”
“你觉得,大王这样,是因为宠爱我吗?”李斯对蔡止说,“君臣之间,本来就不存在等价交换的关系,君主即使要处死臣子,臣子也得领命。
“作为臣子,我没有办法拒绝大王的赏赐,而有了这个赏赐,就相当于是有了把柄在大王手里。
“今后他要做什么,只要我不同意,就可以拿出这件事来,要我还人情,大王的人情哪里还的完呢?
“大王主动施恩于我,看似是对我的关心,其实是只是帝王的权术之法而已。而我虽然看破了这一层,却没有任何的办法,还有什么好开心的呢?”李斯说。
蔡止听后不知该如何应答,只能先指挥属官赶快回原位办公,自己把李斯扶到内室休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