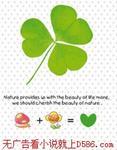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天法道 道法自然 > 第29章 禅佛长生(第3页)
第29章 禅佛长生(第3页)
那济尘且是回了心性,恍若梦中惊醒。且是口中高悬佛号,合掌向那程鹤,谢道: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多谢施主……”
重阳刚要说话,便被程鹤在他手上捏了一下,顺便接了包裹,重新包好放在身边道:
“鹤,请见将军为得三事……”那宋粲听罢,心道,这是要说正事了,遂欠身道:
“兄长请讲。”那程鹤捻指思忖道:
“一者,为这窑卷火经。”
那宋粲听罢倒是一奇,这瓷贡“窑卷火经”便是且须每年经的地方有司上报工、礼二部,那郎中处亦有存放。这程鹤怎的有此一问?且是为何也?想罢,且又不敢打断,便望那程鹤听他下言。
见那程鹤继续道:
“家父自来汝州,曾命汝州各窑将历年窑卷火经汇于草堂……”话未说完,便又捻指一番,怔怔道:
“然,经癸字研读,不实之处甚多,使得推算偏差巨大……”说罢且又若有所思,片刻又喃喃:
“鹤,度之……盖因各窑炉敝屣自珍,或子侄传承,不肯以实情相告……”说罢,便拱手于那宋粲:
“此事,还得烦劳将军与之通融。”
宋粲听罢,自度此乃小事,便将手一挥,轻松道:
“这有何难?可下文牒,令各司衙再行收录,兄以为如何?”
此言一出,便见那程鹤一愣,那眼神倒让那宋粲有些不自在。赶忙用眼神询问,却见那程鹤摆手,道:
“嗨,如用司衙,定是与我家大人收录无异也,也会平白让那些窑主受些牵连。”
听到程鹤言语,宋粲便“哦?”打了一个问询。
程鹤见宋粲不解,便笑了回道:
“如再行收录,两次相同还则罢了,如若不同,则有欺瞒之嫌。将军又是这制使钦差,这欺上……”程鹤说罢,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眼睛则看向宋粲。宋粲看罢饶是心下一惊。低头细想来,此话饶是在理,倒是自家孟浪了。
思忖左右却也一时想不出个好的办法,便低头道:
“这倒难办,容弟再思之……”
那程鹤见那宋粲如此,便是宽心道:
“不妨,兄来汝州不过半月,却抵得过家父五年之功也。”
闻程鹤如此说,宋粲到也觉得不好意思了。赶紧摆了手道:
“此话怎叫我如何担待?兄谬赞矣。”
且刚想抱拳谢过,却见程鹤起身拱手道:
“鹤,代家父请将军用人脉以私情为之……不知当否?”
宋粲赶紧起身回礼。心下盘算,不晓得这程鹤口中之“人脉私情”为何?倒是心下想道拿诰命夫人,想必那程鹤言中所指便是她了。此事倒是不难,只是失些面皮问那诰命夫人讨之便罢,想罢道:
“姑且可一试……”
听得宋粲如此回答,程鹤便整衣再拜道:
“大德不可言谢,鹤代家父拜之!”
宋粲赶紧还礼,口中道:
“兄长不可如此……且坐了说话吧。这一句一磕头的且是个难捱。”
此话且是让那在座众人哈哈大笑。于是乎两人又重新落座。程鹤道:
“这二者,则为这长生济尘禅师而来。”
言到禅师,那和尚便起身双手合十见礼,那宋粲只是抱拳回了过去,未直接和济尘说话,却转脸对程鹤道:
“这长生在饶是在那京中如雷贯耳也。且不说在下有家训耳提面命,便是这制使钦差钦命督窑,亦断不可与其有些许交割。此情,望兄海涵。”
程鹤听闻宋粲如此说话,便面上尴尬,随即又笑道:
“素闻将军家风,以德善治家,持心如水,乃医帅医者风骨。这十日内已是如雷贯耳,眼见得实。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