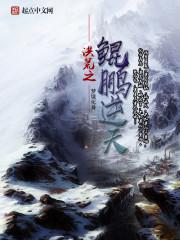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一把燃 兔子撩月 > 第106章(第1页)
第106章(第1页)
两人一怔,只听轰隆隆的响声从身后传来。
伴随着巨响,他们看见刚抵达机场的郜大队长已驾驶着飞机,自他们身后起飞,率先冲向了高空。
见状,两人都不假思索地即刻向工作人员比了手势,操作着飞机,一前一后顶着暴雨重新起飞,如离弦的箭一样,射向了阴云密布的天际。
升至高空时,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声,他们便见一阵黑烟从雨雾中徐缓飘散开来,而一架纹着膏药旗的96式轰炸机如燃烧的火球,机尾拖着浓烟,从高空陨落。
一下明白过来,是郜大队长旗开得胜,击中了敌机的油箱,他们倍感鼓舞。
良凛然和其余赶来的队员们纷纷飞向郜大队长的飞机,替他做掩护。而郭阡忽然在白色云团中瞥见了一抹迷彩色,当即警觉起来,冲下云层,追击那团迷彩而去。
眼前的迷彩飞机忽隐忽现,狡猾地躲进了一团黑云,利用黑云做掩护,和郭阡玩起了捉迷藏。郭阡干脆利落地提速,想要追击上这架敌机,却听一阵弹雨“铮铮”地打在他的机翼上,留下了几个黑洞洞的枪眼。
他连忙拉着操纵杆,将飞机旋转了个角度,翻滚避开了又一波子弹攻击,与此同时也对准了他在云层罅隙中窥见的敌机机尾,连按按钮。
十几发子弹狠厉地飞向敌机,后座枪手身中流弹,瞬时殒命,而敌机也放缓了行进速度。
郭阡抓住时机,穿云过雨,仰冲而去,紧咬着敌机的尾巴不放。他与敌机的距离一点点缩小着,逐渐能看见敌机的全貌——是一架双尾翅的轰炸机。
机不可失,他没有半分犹豫地瞄准了敌机的油箱,开火射击。
8月14日的广州也是大雨滂沱的,白鹅潭的生意冷冷清清的,客人们都在家避雨,也没再来白鹅潭寻乐子。
小翠姐约了一帮姐妹来打麻将,三缺一,也叫朱鱼去她那儿凑个数。
朱鱼的运道和牌技都很差,今夜还动不动分神,被小翠姐察觉到,讪笑着奚落她:“人都走了一年半多了,还不习惯?成日里失魂落魄的,不晓得的,还以为他把你的魂都带走了。”
阿媛姐意识到她在说郭阡,替朱鱼打圆场:“嗳,小年轻们谈起恋爱就是这样的咯,脑子里分分秒秒一直在想着对方,不是很正常的么?”
“正常什么正常呀?”阿翠姐摸了一张牌,又打出一张“六条”,“成天跟守活寡似的,还叫正常?早叫你别去招惹他,你不听,自己反倒现下活受罪。”
朱鱼听了沉不住气,摸了一张牌,见刚好是她要的牌,将牌一推:“胡了。”
说完也不等她们给钱,兀自走出了船舱,淋雨跳回自己的船上。
思念和江水一样漫延上涨,她坐在船头,正在思念他时,就听见一个嘹亮的女音疾声从雨幕里传来:“朱鱼——朱鱼——”
闻声,朱鱼抹了把雨水,朝岸边望去。
瓢泼大雨里,郭蔚槿身着红裙,撑着伞,像一簇跳跃的烟火,向她的船跑来:“打胜仗了!打胜仗了!他们打胜了!”
朱鱼立马翻身下船,不顾一切地向郭蔚槿疾奔而去:“二姐,你是说……雁晖他们打胜仗了?”
“我在《东南日报》的朋友刚给我打来电话,说是今日下午阿阡他们大队飞去杭州作战了,总共击落了3架敌机,阿阡他也击落了1架。”郭蔚槿激动不已,不顾大雨,将伞一下扔开,和朱鱼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无一伤亡,半小时不到,就把敌机全都打跑了!”
朱鱼喜不自胜,和郭蔚槿热烈地拥抱。两人在大雨里淋着雨,为这难得的胜利,又哭又笑。
那时,沉浸在快乐中的她们尚且未知的是,广州城的安生日子很快便将一去不复返。
半个多月后,日军的飞机如蝗虫过境一般,遮天蔽日,浩浩荡荡飞向了广州城,对广州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狂轰滥炸,将广州这昔日的不夜之城变为了人间炼狱。
另一边,在杭州的夜里,打了胜仗的英雄们却都难以入眠。
除了激动以外,更多的是杭州闷热的天气和蚊子令人不堪其扰,无法入眠。
他们只带了简单的寝具来杭州,而笕桥也没为他们安排住宿,只能让他们宿在办公室里喂蚊子。
良凛然在郭阡旁边打了地铺,烦不胜烦地用手拍死嗡嗡乱叫的蚊子。
他转眼一望,望见郭阡伏在被窝里,一手举着打火机,一手握着笔,继续在写那封没写完的家书,不由将脑袋凑过去看:“都写了这么久了,还没写完啊?”
“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当然要多写些话。别来烦我,打你的蚊子去。”
良凛然死皮赖脸地缠着他,不让他写下去,最后还耍起了赖皮:“你给我看一眼她的照片,我就不来吵你了。”
郭阡笑了一声:“你说谁的照片?”
良凛然总算服了软:“我阿嫂的照片。”
郭阡又笑了笑,才从怀里掏出了那张蔡栩言刚给他寄来的照片——也是他和朱鱼在蔡栩言的婚礼上,唯一的一张合照:“好看不好看?”
良凛然笑出了大白牙,在一片暗中都映出火光了:“嘿嘿,比你是好看不少。怪不得以前在航校,有女孩子来送你情书,你睬都不睬她们。”
郭阡一掌拍开他的脑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