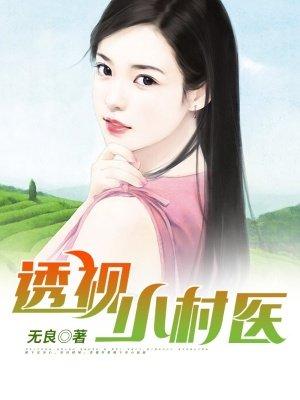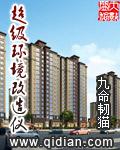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猎杀U舰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他的想法随即获得舰队长的支持,宣达之后,全舰都受到了鼓舞。
管他上浮以后会怎么样,上浮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事。
想到上浮,大家又紧张起来。不是害怕海面有什么敌人,而是忧虑离开海底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说出来虽然有点丢人,但却是事实。即使是舰长萧念宗,这次坐底也是他潜舰生涯的第一次。
是的,第一次。
不是他们平常疏于训练,而是潜舰教令有规定:非到逃命的必要时刻,不可以冒险坐底。
中华民国海军潜舰部队近五十年的历史中,一艘潜舰面对「逃命的必要时刻」,这还是第一次。
潜舰不轻易坐底,因为坐底充满了未知与挑战。首先要忧虑海底的礁石是否会伤到靠近船底的装备,例如测深仪、舷侧下方的被动式声纳、舰艉的车叶和十字舵。就算装备逃过一劫,船底有各式各样的排水与进水孔
,它们会不会因淤泥而堵塞?
另外,坐底的深度更是值得忧虑的问题。
潜舰潜航不论在任何深度,都尽可能保持和海水同比重。除非「紧急上浮」,它不会从很深的海底直接往上冲,而是先到达潜望镜深度,确定水面安全,再释放高压空气排除「主压舱柜」的海水。
一艘柴油潜舰珍贵的资源,也是他们救命的资源,有两种。一种是电瓶电量,另一种是高压空气。每次上浮,柴油潜舰先启动发电机充电,接着就启动空气压缩机充气。而高压空气瓶的设计,是以能提供潜舰在「潜望镜深度上浮几次」来计算;或是说,能排除几次「主压舱柜」里的海水来计算。
老式柴油潜舰受限于空气压缩机的能力,只能提供五至七次上浮的高压空气。纪壮舰使用最新式的空气压缩机,空气的压力虽然增加,但是因储存瓶的体积相对变小,至多也只能提供「十单位」上浮的高压空气。
现在问题来了||纪壮舰坐底的深度是一百七十四公尺,和潜望镜深度足足差了七倍的水压;想要排除同体积的海水,需要消耗的高压空气就必须是平常的七倍。
更麻烦的是,纪壮舰前次上浮消耗「一单位」的高压空气,紧急下潜灌入「一单位」的海水,坐底又灌入
「零点五单位」的海水。假如一切都合乎理想,现在排除「零点五单位」海水||消耗「三点五单位」的空压空气||可以回复与海水同比重;想要到达「浮出海面」的比重,还需要七单位的高压空气。
当然,并不是说纪壮舰要脱离海底,一开始就需要十点五单位的高压空气。理论上来讲,先释放三点五单位高压空气,舰体比重就应该和海水相同;之后再多释放高压空气,不管量多量少,都会让船的比重小于海水
,纪壮舰也就应该开始上浮。
但是,理论归理论,现实往往又是另一回事。
萧念宗和轮机长寥沛元经过再三讨论,由于纪壮舰此时是「头重脚轻」||舰艏下俯十七度;他们决定先释放两单位高压空气到「后主压舱柜」||让船艉更轻;假如因而船艉能往上抬,抬动的瞬间就释放四单位的高压空气到舰艏||「前主压舱柜」和「紧急压舱柜」各两单位;总共六单位的高压空气,纪壮舰就应该会慢慢往上浮。
一旦上浮,纪壮舰因坐底而产生的危机就能解除。
决定了以后,轮机长亲自来到控制室,透过声力电话将舰长的命令传给李成汉。李成汉是辅机士官长,他人在机舱,指挥三名在不同部位的士官,用人力方式操控高压空气释放的路径。
萧念宗两眼盯着「纵倾角指示器」,竖起两根手指朝舰艉比了比。
轮机长低声下令:「高压空气,两单位,后主压舱柜。」
在前所未有的寂静之后,高压空气奔腾的「嘶」声显得前所未有的刺耳,甚至到头痛欲裂的地步。所有人都不自禁地张张口、堵住耳朵,以便释放耳膜的压力。
等到「嘶」声消失,舰体却稳如泰山,纵倾角没有任何改变。
萧念宗双手各竖起两根指头,同时指向船头的方向。
「前主压舱柜、紧急压舱柜,高压空气,各两单位。」
又是刺耳的「嘶」,时间拉得更长。但是当四下回复寂静,舰体依旧不动如山。
萧念宗先瞥了眼高压空气瓶含量||三单位,再看看电瓶容量||三七%,痛苦地考虑了一下,目光转向航海士官长林宗伦,毅然令道:「备车。」
备车是启动主机;主机经过减速齿轮带动大轴,舰艉车叶才开始以每分钟三十三转的速度顺时钟旋转。这时车叶的螺距角在零度,只是空转,不会产生任何前进或后退的力量。
先前没有备车,是因为舰体紧贴着海底,转动的车叶可能会打到礁石。
林士官长回报「已备车」,轮机长随即询问大轴旋转状况。等机舱回报有轻微震动,他忧心忡忡地向舰长说明。
萧念宗摇摇头,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下令:「后退五。」
林士官长把车速操纵杆往后扳,指针停在「五」的位置。
舰体几乎没有任何震动,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萧念宗侧耳聆听片刻,的确没听到异声,有点怀疑地看了看纵倾角指示器,接续下令:「后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