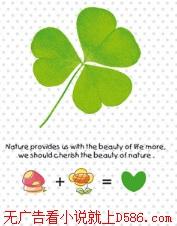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得咎全文加番外在线 > 第七章(第1页)
第七章(第1页)
在那场弥漫着血腥味的混乱之後,裴文歌
裴文歌在医院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他对身体上的感知极其的迟钝,等到他
下午二点锺,崭新且整洁得几乎看不见灰尘的机场里,抵达的旅客陆续从通道出来,他们拖着行李箱,男男女女,多以一种愉快期盼的容貌,在等候的人群中寻找熟悉的人。也有人很是疲惫不堪,不断地掏着因气压不平衡造成疼痛的耳朵,摇头晃脑地疾步而走。
大堂的广播扬起柔美的女音,她播报着已抵达的航班,以及延误了的班次。
在接机区的人群中,有四个黑衣男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低声交谈着什麽,视线却一刻也没离开出口,犀利的不露痕迹的,在每一个经过的人身上巡过……直到那道颀长伟岸的身影出现了,他们方才止住了话,郑重且恭敬地迎接了上去。
容沛还是这极吸引人注意力的存在。随便的任何装扮在挂在他身上,全就撑架出了一种足以人欣赏的品位。
他穿着白色的无袖汗衫,外边加了一件剪裁合适的黑色外套,黑色皮带扣上镶了r的字母,蓝色的牛仔裤,长腿更显笔直挺拔。
人们窥视着他。这是个俊美的年轻人,短发梳理出略带凌乱的发型,那张过分精致的脸蛋上戴着墨镜,架在鼻梁上,遮住了他有些淡漠的偏褐色的眼眸,这让人不由得多注意他的唇,很凉薄的形状,粉白的色泽更适合女人。
他在国外的这两年,竟显得比从前更加高大了,肤色则仍旧异常的白皙。不再是过去年少轻狂的少年了,已有了成熟男人的味道。
前来接机的保镖接过了他的行李,他们两个在前,两个在後,簇拥保护着他和他身边的女人走出了机场大门。
机场外停着两层巴士,还有计程车,他们在极有秩序地等待。机场的制服保安站在门两边,对他们一行人看了几眼。
这是10月份了,清晨及傍晚时还有了凉意,下午则依然没有摆脱夏天的燥热。容沛站在机场的门前,有两个保镖去停车场开车,他仰起头,享受着阳光照拂在他脸上的温度,随後,很自然地牵住了身边的女人,那是他订婚一年多的未婚妻,凯瑟琳。
这次回国,他们会举办正式的婚礼,结为夫妻。
凯瑟琳是个混血儿,父亲很早就移民国外了,後来娶了当地最美丽的姑娘,她在国外出生,接受的是国外的教育,但还是会说中文,只是老夹带着奇怪的口音。
她在四周来回环顾着,身边经过的人,机场的建设,周围的建筑物,颇为感兴趣。在回国之前,容沛就事先和她说了,在容家生活必须讲中文,她得习惯这点,於是她搂着容沛的胳膊,用她奇怪的口音,说:“容,这就是你长大的国家?”
容沛轻轻应了一声,无视行人或艳羡或惊讶的窥视,顺势搂住了她的腰,这时两辆黑色的轿车滑到他面前,他给她打开车门,扶她坐了进去。
他温柔体贴得就像个绅士,谁也无法联想到这样一个贵公子,曾经那样暴虐的对待过另一个人。
在前往容宅的路上,凯瑟琳快活极了,这个陌生的国度对她太稀奇了。她一路上问了许多问题,容沛都很耐心地为她解答了,他同时也在打量着这个城市,分心之余,也在分辨着它的变化。
他在国外的这两年,全新的生活,全新的环境,他交新的朋友,上新的学校,读新的课程,也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随心所欲地享乐,也和所有试图找他麻烦的人打架,不用他的家世,而是用他的拳头赢得别人的臣服。
他高傲自满,他生活排得满满当当的。他很少很少回想起出国前的一切,所有新鲜的事物充斥着他的所见所闻,让他没闲暇去顾其它,那些和某个人有关回忆都像是被他压缩打包成了一份行李,结果却忘记带着它登机了,只把它遗留机场的一个角落里,成为被人清扫掉的垃圾。
爷爷过世的时候,他只是非常短暂的停留,甚至没来得及看看这里的变化,他就又走了。现在他回来了,是真正回来了。
这个城市变化是有的,却不大明显。容家那座宅子里,应该也什麽都没变吧,就算有,大概也是无关紧要的人。
容沛闲极无聊地望着窗外,各样的街景从窗外一幕幕飞掠而过,这街道宽敞整洁,绿化带上的植物生机盎然,他想着有的没的,车内只有自己和凯瑟琳的交谈声,显得有些静寂。
没多久,他回到了那熟悉的庭院,见到了那块小时候自己追逐奔跑过的草坪,石道旁的游泳池清澈得泛蓝绿的颜色,那喷泉还是沸腾着甘甜的泉水,只是上边的树已经换成水晶雕刻的,也看不出是什麽树儿,枝叶上的花一朵挨一朵,朵朵怒放,在阳光和水液的映照下,焕发着夺人目的璀璨。
车子缓缓驶进了停车位,容沛收回了视线,摘下了墨镜,保镖为他开了门,他下了车,等待着凯瑟琳,在她下来时牵住了她的手。
凯瑟琳毫不掩饰自己惊喜的模样,容沛的家比她所预知的要好太多了,她扑到了他的怀里,大叫着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容沛忍受着她在他耳边的尖锐的嗓音,没发脾气,他拥抱着怀里柔软的女人的身躯,拥抱紧她了,也朗声笑了,哄着她,让她冷静。他追求这个女人时,是又一次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
容沛年轻的岁月中,遇见好多次真爱,结果他真的那份爱,却在追逐中被他遗落了。
而此时此刻,他的真爱在他的怀里撒娇,他感染着她的快乐,嘴里说着许多哄人的话,可是面向自己家的那栋房子,它在午後静静地屹立着,每一砖每一瓦都是他记得的位置,却忽然予他一丝莫名的陌生感。
他还是在哄着他的爱人,刚到家,刚下车,就站在自己惯用的车位旁,现在这和他以往很多次出门後回来一样,不同的是他有了将要共度一生的女人。
出於某种习惯,甚至自己也没发觉,他的眼角往後一瞥,不同的是在他右後方的位置,那儿什麽人也没有。只有一棵以前没有的树,树干瘦瘦的,受不住风雨摧残,不若某个人那样,沈沈稳稳的,一望便知他百折不挠的品质。
容太太出现在了主屋的门前,她还是那样的雍容华贵,远远眺望见了她心系的人,便如天下所有的母亲一般,满面漾起了慈爱的笑容,举起手臂朝他们招手,催促着他们靠近。
容沛摆脱了那点儿异样,他不想母亲久等,便拍了拍凯瑟琳的後背,她却还是无法乖顺下来,仍在他怀里扭个没完,令他不禁奇怪,原来住进这样的环境能让人这麽快乐,接着另外一点儿奇怪的念头闪了过去:这个房子有人住了十几年呢,那人也没见有开心。
那人
晚饭过後,客厅那盏夸张的吊灯打开了。
佣人端来了一个果盘放在茶几上,各样鲜甜的水果在盘子摆得实是漂亮,果肉上洒着点点水珠,并用果皮切割出了造型。
容沛拿着小银叉刺了一块苹果,放到齿间一咬,果汁在舌尖上晕开了去,往大脑里传去了一个信号,这水果的味道没有异样。他又连续咽下去好几块,嘴里的口感好了很多,现在他都记不得刚刚是吃了什麽了。
而容太太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着,那条泰迪犬又冒出头了,她把它抱在腿上,竟将它当做一个小孩儿对待,正在给它梳理毛发,动作细致轻柔,手边还摆着件薄薄的红毛衣。红毛衣很小很小,正是适合狗的体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