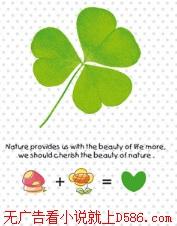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白鸽玫瑰图片 > 第88页(第1页)
第88页(第1页)
男人仔细地看着,最后指着衣角确定地点了点头。“认识,这件衣服是我以前室友的,当时我们寝室六个人都有一件同样的衣服,为了区别,就用不同颜色的线把衣角重新缝了一遍。”顾潇低头看向衣角边缘,果然有一道蓝色的线缝。“这件是蓝色的,蓝色应该是……”男人想了想,突然一拍手,“对,是何凛,没错,他用的蓝色。”顿时,顾潇整个人像是被定格了一样,惊讶地张着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这件衣服是何凛的?!”“是啊,当年他说衣服丢了,同学,你认识他吗?我记得他大二就休学参军去了……”男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顾潇已经听不清了。那年,在她最恐惧最无助的时候,突然出现挡在她面前,赶走了那群企图欺辱她的社会青年并给她披上这件衣服的大学生,竟会是何凛。原来,他们早已相遇过。雨点斜落,飘进了伞下,打湿了肩头。太阳从海平线上露出头,把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橙色,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空气中弥漫着海盐和新鲜海藻的混合气味。远处的海平线上,一艘渔船缓缓驶过,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尾迹。顾潇赤脚走在沙滩上,细软的沙子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偶尔,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了海水的清凉和远处鱼儿的淡淡腥味。海鸥在海面上盘旋,不时地发出欢快的叫声,给这片海域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今天是来到这里的番外:如愿沈岳进来的时候,看到何凛坐在窗边,凝神望着外面。顾潇蹲在对面的屋檐下,和迪莉娅一起逗弄着小猫,她似乎是笑着,却又似乎失掉了什么。沈岳叹了口气,“她明天就要走了,你真的不打算让她知道你还活着?还是你准备在她走之前,就一直这样躲在这里偷看?”何凛回过神来,关了窗,推着轮椅转了过来。“对她而言,不知道更好。”“你是没看见她那天有多伤心,我认识她以来从来都没见她那样痛苦过。”“医生都说不能确定我还能不能站起来,何必让她失望?”“其实我觉得对顾潇来说,你活着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她不会在乎。”“但我不能不在乎。”何凛的声音沉闷,竭力抑制着不够稳定的情绪。“沈岳,当初你为什么坚持和知羽分手?”“我……在说你和顾潇,怎么扯到我和知羽了?”“你知道她没有结婚,为什么不去找她?”“……”沈岳眼神黯然,无言以对。“所以,你不应该是那个最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的人吗?”“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劝你了……对了,昨晚打雷,你还好吧?”“睡得沉,没感觉到痛。”“真的不痛了吗?”“好像是不痛了。”何凛摸着头,八年间折磨得他痛不欲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不知不觉地痊愈了。第二天,顾潇提着简单的行李上了来接她的专车。沈岳,迪莉娅,弗朗来送行,但谁都没怎么说话。上车前,她又往远处看去,也不知道是想看什么,留恋吗,不是,也只是望着发了会儿呆,直到沈岳提醒她,这才回过头去,上了车离开。她并不知道,就在她回头望的那一瞬,那棵大树后,何凛坐在轮椅上,忙不迭地把自己藏到了树干后,就差一点点,她就发现他了。车驶离了视线范围,沈岳走了过来。何凛还在看着车远去的方向。“她走了?”“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何凛点点头,眼中似有失落。沈岳过来推他,两人往回走着,太阳升出了山头,就像他们在这里经历的每一天那样,什么都没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昨天专家会诊之后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之后只要坚持做康复训练,用上个月是能恢复的。”“嗯。”何凛淡淡地应了一声,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两人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聊着些没盐没味的话,都有些心事重重。“何凛,顾潇这一走,你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我知道。”“你就一点都不遗憾吗?”“当时你离开知羽,遗憾吗?”“我跟顾潇说过知羽的事情,我说遗憾是人生常态,当时她说她接受不了,但是昨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问我,短暂地在一起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结果她自己回答了……”“她……怎么回答的?”“她说,‘我不贪心便是奖励,我不期待便不是惩罚’。”何凛沉默了一阵,轻笑。“这就是顾潇。”“何凛,可能你自己没有发现,自从认识顾潇之后,你变了很多。”“是吗?”沈岳肯定地点头。“人这一生,遇到爱,遇到幸与不幸,都没什么稀罕的,稀罕的是遇到了解,遇到那个能透过刻板的面具去了解我们,能够愿意去听我们的恐惧,担忧,胆怯,会让我们毫无保留地放下戒备,不用再伪装自己的人,才是一生最可贵的事。”听着这话,何凛又想起了那晚在山洞里,顾潇没有说出口的“最后一句”。对于这个,他还是多少有些在意的。其实他知道是哪一句,以前段云念还在的时候,很喜欢西方的现代诗歌,所以他记得,这是一首诗,名字叫《手捧希望而来》,但听顾潇念起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惊讶的,像是对这种巧合来得有些猝不及防而不知所措,又像是心里有什么不能言说的隐秘即将被揭穿的慌乱。